
说起传统上海菜,除了公认的选料注重活、生、脆、鲜,调味擅长咸、甜、糟、酸之外,好像跟“辣”字沾不上边。不过如今,似乎上海人越来越能吃辣。响油鳝糊,要来上一把辣椒,再倒滚油;白斩鸡,得埋在一堆泡椒里;就连清蒸鲈鱼,也须摆一层剁椒上身。
上海人也开始吃辣,有些人是属于幸运,在娘肚子里就已开始吃香喝辣的;还有些人,则是从后天的酸甜苦辣中,慢慢炼成的。我肯定是属于后者。
四十多年前,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的一个宿舍里,住着七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学子。当时宿舍的标配,是每间四个高低床,分开两边靠墙而置。中间两张长条桌,既是书桌,又是餐桌。八个床位,除了一张用来放行李之外,七张床铺住七位学生。我们那个寝室,除了三个上海本地生之外,还有四位外地生,分别来自四川、湖南、湖北和河北。
表面上看,似乎是七拼八凑,七上八下;实际上,却是七步奇才齐聚,七纵八横合成。
两个月的暑假过完,室友纷纷从各地返校上课,一个个被夏天的太阳晒得乌漆墨黑。但是,每个人都像是光伏电池充满了电,浑身是劲。最带劲的,就是每个外地同学都带来了家乡的土特产。除了一些小吃零食之外,居然都是家乡特色的辣椒:河北的辣椒面,湖南和湖北的辣椒酱,四川的牛肉辣椒酱,令上海同学大开眼界。
辣椒算不上是什么高档食材,而且当时的包装也相当简单,说不上是风情万种。但室友不约而同,都把乡村的辣椒带到大都市的高等学府,那肯定是对家乡味道的情有独钟。
问题来了。究竟是哪里的辣椒酱最辣?湖南湖北学子据理力争,河北四川同学互不相让。接着,争论马上转移到究竟谁最能吃辣?于是乎,各地同学,引经据典,争得面红脖子粗。
这个话题,上海同学就没有资格参与了,只能在一边窃窃私语,猜测着哪种最好吃。
记不得是谁,忽然提议,不如来一场吃辣椒比赛,看看到底谁最能吃辣,评判一下谁家的辣椒最辣,最好吃。全寝室一致同意。于是大家就着食堂买回的淡馒头,一起参与了一场友谊品尝赛。
一堆白馒头很快就被消灭了,顺带消灭的,还有四五个老式热水瓶里的开水。猜猜看,比赛结果会怎样?
结果是大家居然无法形成共识,分出高低。彼此依然像是王婆卖瓜,吵成一团。
我在品尝了辣椒面的干辣、辣椒酱的湿辣、牛肉辣椒酱的油辣之后,虽然嘴里已经又辣又麻,说不上话,但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:还是牛肉辣椒酱更胜一筹。因为它有辣椒油的香,还有牛肉味的鲜。在那还是无肉不欢的年龄和年代,带牛肉粒的辣椒酱自然更有吸引力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,从食堂打饭回来,就看见室友各自拿出家乡的辣椒,就着当时缺油少盐的乏味饭菜,居然吃得津津有味。看得出,辣椒对室友来说,不只是一种乡愁,也似乎,是一种“刚需”。
这种既解馋又解乡愁的真实感觉,在自己出国以后才有了亲身体验。
第一次出国,是赴莫斯科大学参加一个联合国项目培训,为期三个月。当时是80年代后半截,当地农产品消费市场正处在崩溃的边缘,商品奇缺。动身前,为了省外汇,更是怕吃不惯俄式一菜一汤(罗宋汤,面包加黄油),于是在行李箱里能用的空间里都填满了方便面,尤其在箱子一角,还塞进了一瓶川味辣椒酱,用袜子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在保尔·柯察金的故乡待了三个月。进修学习之余,有幸观赏了原汁原味的《天鹅湖》,品尝了令人食指大动的鱼子酱,领略了一碗不过岗的伏特加。但在日复一日的一菜一汤前,难免望而却步。幸亏有方便面和四川辣酱“续命”。烧一壶水,泡一包面,加一根俄式小香肠,再放一勺辣椒酱,刹那间,满屋香气飘溢。连汤带面送入口中,独特的辛辣在口中迸发,味蕾在幸福中跳舞。中国辣的基因,觉醒了。
再后来,来到了被称为亚洲之外最亚洲的城市——温哥华,发现这里居然川菜、湘菜、滇菜,烧烤店、火锅店,应有尽有。东西南北各方辣味,齐聚云城,形成了当地“辣市”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一次,和几位上海老乡相约,走进一家列治文的火锅店。只见墙上写着:“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,如果有,就再来一顿。”就这样,来了一顿又一顿,倒并不是因为事多未决,而是好这一口。
偶回沪小住,只见大大小小餐馆里,菜单上有些地方都已标上大辣、中辣、小辣的选项。忽然好像明白了,上海上海,来自五湖四海,融汇风味东西。有辣和能吃辣的人,才使沪上百味人生,更加丰富多彩。
上海人吃辣,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。(半 张)
(图片来源网络侵删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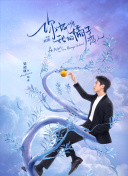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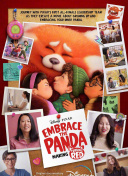



发表评论
2024-05-31 18:36:38回复
2024-05-31 18:40:01回复
2024-05-31 18:43:35回复
2024-05-31 18:46:53回复
2024-05-31 18:49:33回复
2024-05-31 18:50:06回复
2024-05-31 18:52:52回复
2024-05-31 18:53:27回复
🤔(思考表情)
2024-05-31 18:54:05回复